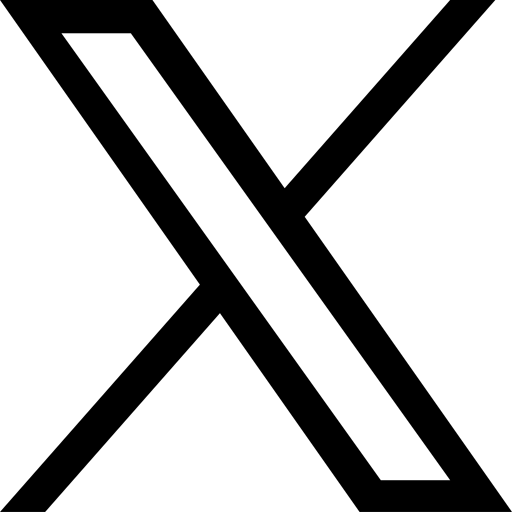2018-01-17Text: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光臨
宋代模式、一帶一路與中國道路
以前學術界關於宋朝經濟發展的研究往往以王安石變法為中心而歸納出一種變法模式,並擴大衍生為「中國歷史上變法為何總是不成功」等問題,這種解讀雖然在近代以來包括改革開放的初始時期鼓舞了人心,其實卻忽略了宋朝模式在世界史上的意義,也簡化了中國歷史。宋朝是承唐末五代歷年戰亂和分裂而出現的一個政權,較之唐代疆域收縮很多,基本局限於漢人居住耕作的地區,而其發展模式也不同於漢唐,軍事動員上大量募兵,高額的軍費開支逼使政府將稅收視為急務,在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開創了以間接稅為基礎的發達公共財政體系,這種發展模式是以國家政權和商人之間的緊密合作為前提,五代以來的軍人政權因為贍軍的財政壓力而被逼斂財,無所不用其極,反覆嘗試之後終於領悟到市場擴張與稅收之間的制度性連接而建立起來。
我曾經對北宋熙寧十年的商稅數據加以分析,發現宋代的商稅收入的地域分布集中於12條河流上,它們貢獻的稅額有397萬多貫,佔全部商稅的一半。而南北向的人工運河和部分人工改造、維修的半天然河道如太湖、漢江等就佔了上述河流的近一半,充分揭示了以水運為基礎的長途貿易是宋代商稅徵收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十到十一世紀以東京開封為中心的發達的水上運輸體系也孕育了以首都為核心的長途貿易網絡。這體現出以市場整合為基礎的國家發展模式,完全不同於中國歷史上其它王朝統治範式。即以多數史學家推崇的漢唐盛世而言,皆為追求領土的擴張和對百姓的人身控制,而宋代法律允許移民自由和擇業自由,鼓勵貿易和城市發展,看似摒棄了「專制」因素,實則是因為其權力以金錢為媒介,只有市場擴張,特別是長途貿易和城市消費才能為政府稅收提供紮實的基礎-這才是宋朝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特色。
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對中國文化制度處處推崇,以為其理想和路徑不同於西方而又高出西方,但是在其所撰國史大綱將漢唐譽為盛世中國的代表,而譴責宋代「積貧積弱」,並歸咎於其制度的集權與無效,這種看法正是忽略了衡量國家能力的不同標準。如果從陸上疆域擴張而言,宋朝不可謂強國的代表;但是從資本與財富的角度看,則宋朝開創了新型近代國家之路。比較而言,歐洲霸權之崛起正是因為其國家精英實施重商主義政策以強化國家能力,將軍事擴張與市場發展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市場越擴張就越能為政府提供穩定增長的稅收,而政府就越擁有財政資源進行戰爭。今人研究作為第一個全球霸權的英國崛起經驗,發現其開始稱霸的基礎不是工業革命,也非民主或者革命,而是其特別的酒類專賣制度和國債發行,可以源源不斷支撐軍事競爭,發展海軍以對抗歐陸強權。我曾將北宋稅收結構與英國比較,兩者相似性是驚人的。進一步說,以軍事動員和財政國家為一體的資本主義體系,其實是緣於宋代中國,只是由於南宋亡於蒙古征服而導致這一稅收國家體系在中國消失,到晚清變法之際,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還以為是向西方學習,卻不知這實際上也是向宋代模式的復歸。
用經濟學話語解釋,宋代模式就是利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幫助實現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既非打擊商人、壓榨市場的命令經濟,也非束手旁觀、相信市場萬能的原教旨自由主義。宋代模式的意義在今天國家推動的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戰略上都是有充分展現。所謂一帶即是圍繞原絲綢之路的亞歐大陸的內部聯系,歷史上並不以貿易為基礎,而是文化、宗教和戰爭推動的交流和融合,蒙元以後終於形成以北京為統治中心的大中國,今天如果進一步推動其發展,就要善於利用文化或者宗教手段,而資本其實很難發揮主導作用,因為這一帶是世界上最廣闊也是最落後的地區,完全沒有市場整合的基礎。
而一路截然不同,其前身就是唐宋變革時代出現的海上絲綢之路,是以低運輸成本為基礎的海洋國際貿易,大灣區的框架也以市場為基礎,則近似宋代以水運、移民、和技術傳播為推動力的南方經濟起飛。所以一路和大灣區的發展邏輯必會體現宋代模式的真正特色:哪裏有市場,哪裏就有國家(制度),兩者相輔相成,在市場制度配合下資本和技術進而大施拳腳。大灣區發展必然以市場整合為基礎來推進高效的產業分工,必然利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幫助市場更好地配置資源,而一路的實現更需要商人和國家的緊密合作,中國政府在世界貿易和全球發展上扮演了推動者和保護人的角色。如此一來,市場整合的深入進步,將帶來技術和分工的巨大進步空間,造福全球,而筆者一再鼓吹的以中國化為特色的新一輪全球化才會有實現的可能。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與拍賣官看藝術】畢加索的市場潛能有多強?亞洲收藏家如何從新角度鑑賞?► 即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