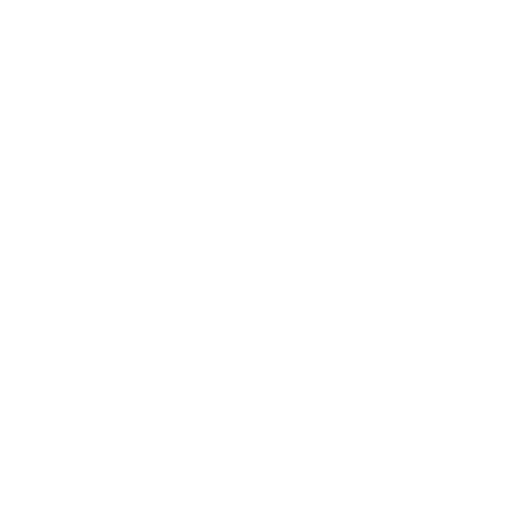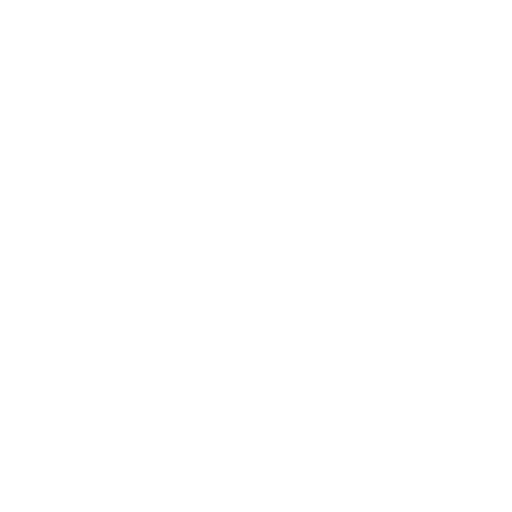06/06/2016
我的考試生涯:一個「放牛班」學生的逆襲
編者按:又是一年高考時,特摘錄郎咸平教授在其著作中披露的個人求學生涯,以鼓勵莘莘學子。
一、從小學到高中:差點去當了木工
我在上小學的時候,成績一直很差。當時,小學一到四年級時我連書都不會念,而且似乎甚麼都不如人家,包括體育、藝術等。我對自己完全不認可,由於當時屬於差學生的緣故,因此內心充滿了自卑感,而且我對未來也不敢有甚麼想法。在小學五年級時,我被分到特別班,由老師對我們這些跟不上進度的學生做特別的輔 導。記得父親在我小學五年級時,拿了一個算術模擬考試的試卷讓我做練習,滿分是100分,我辛辛苦苦地做完以後,卻只得了5分,那個算數題目特難做,我根 本沒有任何概念。還好,就在我六年級時,小學生就不用考初中了,於是我成為了臺灣地區第一屆小學直升初中的學生。
我進了大同中 學念初中。我們那一年級有26個班,我被分到15班。我們的班主任黃升煥凶極了,他就是那種在日本帝國主義教育下成長的日本式的大男人。眼鏡圓圓的,他最喜歡耍弄日本武士刀,還經常給我們看他的武士刀,我們羡慕得要命。為了有效地控制班上的學生,黃老師就學習日本傳統--指定密探,將喜歡上課講話或做小動 作的學生名字記下來,下課後再逐一修理。密探都由班裡前10名的學生來做,他們不會登記好學生,專門登記差學生。班裏總共有50多個人,但班上經常挨打的 差學生有20多個人。我的學習成績不好,屬於那種經常被打的學生。而且好學生坐的位置也好,差學生就坐在教室的四周或最後面,我當時就坐在最後面。黃老師 打人的花樣很多,有時叫我們匍匐前進在地上爬,爬得越慢打得越凶,爬起來又坐在桌子上打大腿,好痛,打手心算是最輕的。
初一念到一半時,我們就搬家了,搬到了離學校很遠的地方,於是我上學要騎車。父親說大同中學好,不要我轉學。因此,每天早上我必須騎一個小時的單車上學,路又遠,車又多,騎車很危險,再加上那個時候老師經常打我,所以我感到上學痛苦極了。
到了初二,由於我的學習成績太差,所以母親就給我找了一個家庭教師補習英文,好像從那以後,我的成績稍微有些起色。有一天,黃老師突然問了我一句話:「這學期家裡是不是有補習呀?」我說:「對。」他好像很不高興,因為我沒有找他補習。
到了初三分班的時候,我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學的班,是供那些沒有出息的差生學習的班,我們當時有七個差同學都被分到「放牛班」了。當 時我心裏還有點憤憤不平,叫母親去找關係幫我弄到升學班裏去,母親說分到什麼班無所謂,只要自己用功即可,她沒時間去管我的事,她要教書賺錢。父親在部隊 裡根本也不知道這件事。沒辦法,我只有乖乖地待在「放牛班」裏了。「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跟太保。因此,從小我就對台灣地區的流氓、太保黑道非常熟 悉。我在學校幾乎是天天打架(基本上都是被打)。初三的時候,我感覺非常不愉快,很討厭上學。
我被分到「放牛班」後幾乎天天挨打,那時真不想念書,想去念陸軍軍官學校。初中畢業後,我也去考過陸軍軍官學校預備班(陸軍幼校),想出來以後當軍人,但由於近視的緣故,體檢沒有通過,否則我當時就考上了,現在可能也是個軍官。到了初三,被分到「放牛班」以後,我才發現自己當時所接觸的同學基本上都是社會最底層的人,而且他們中很多都是 家庭很貧困的同學。
在「放牛班」時,我學木工,準備出來就業之用,到現在我的木工還是做得很好,只是目前無用武之地而已。當時,我先學木工,準備再學電工。但我的電工學得不太好,好像我對電子線路不太上手,學了一個學期之後,發現不行,因此將精力全部投入學習木工上面了。我們 學校當時還有實習工廠,工廠裡面有車床、刨床、鋸床等等,工具很全。我木工練得很好,準備出來先做木工學徒,再開個木工廠。我可以把一棵樹做成一套漂亮的家具。那時候,我們戴著粗的白手套,十幾個人搬一棵樹,我們有一個大機器,我也不曉得叫甚麼名字了,把位置調好以後,把樹放進去,出來就是長方形的木板, 長方形木板再放到另外一個機床裏進行切割,要幾塊板就切幾塊板,很方便。工廠裏有一個鋸床,鋸子就在鋸床中間快速地轉動,一不小心就會將整根手指割下,我們使用這台機器的時候都非常的小心。我們那個小組就能把木板切割成任何想要的形狀,到最後再用細刀具、沙具磨,磨得很漂亮,做任何家具都沒有問題。我們 「放牛班」出來的很多同學當了木匠、水泥匠,有的還當了包工頭,承包建築工程,也有的同學當了老闆。從「放牛班」出來再升學的學生基本上只有去念職業學校 了,到最後念到大學的據我所知只有兩位學生,其中一位就是我。
那時候,看到學習成績好的同學,我就很羡慕,心裡的自卑感也很 強。到現在,學校幾個第一名的同學,我都還記得他們的名字。15班的第一名叫陳紹華,還有一個3班第一名的同學叫馬學勇,我對他們簡直崇拜極了。有一次, 陳紹華向我借水彩,我覺得好光榮,他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感謝,我當時覺得激動極了。3班的馬學勇可以說是我所在的年級裡最聰明的學生了,他經常考全校 第一名,但他根本沒有向我借過水彩。馬學勇考上了最好的高中--臺灣「建國」中學,然後又考到台灣大學電機系。
在考高中之前, 我一直沒有好好念書,我在努力地做木工。到臨考的前三個月舉行模擬考試時,在10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800多名,在當時看來我的未來是沒什麼希望了。 馬學勇、陳紹華都是前三名,我每天還夢想著把我的水彩借給他們兩個用。想想800多名的這種成績就算考軍校恐怕也不行。當時,我潛意識裡還是想升學的。就 這樣在考前三個月的時候,我感到了壓力,就想好好念書了。但是,念課本肯定是來不及了,於是我就只好念《考前30分》。大家可能會問我什麼叫《考前30 分》?比如說整個6冊的歷史課本可以濃縮成那麼1小本《考前30分》,50頁左右(A4紙的1/3大小),那是給考生在考前30分鐘複習用的。別人考歷史 得讀6大本,而我只看1小本。反正考6科嘛,我就隨便買了6小本來讀。臨考前的兩個月,第二次模擬考試我考了500多名,臨考試前的一個月,第三次模擬考 試我考到300多名。然後參加考試時,我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願。我的第一志願是「建國「中學,第二志願是師大附中,第三志願是成功中學,當時以我的水 平而言能考上第三志願是很了不起的了。我們整個學校考上高中的總共不到300人,而我能夠在1000多人中,考上這個學校已經很不容易了。當時,在很多種 版本的《考前30分》中,就只有我買的那種抓題抓得最準了。我也不曉得為何我會選擇那一種《考前30分》,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當時買別的版本的 《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嗎,那真的就只有當木工了。
我當時感到很無奈,在初中一、二年級時,成績其實也不算太差,在 30-40名之間,屬於中下等。我們班上還有很多40名以後的同學,但最後我發現他們沒有去「放牛班」。於是,我就一直在想為什麼我要去「放牛班」,而他 們不用去呢?這個問題我一直就想不明白。我想唯一比較可能的解釋就是我沒有補習,而那些40名以後的同學大部分都去老師家補習了。那時,我非常難過,因為 整個事情是不可更改的,而我又是無能為力的,更談不上反抗了,差學生還有甚麼資格反抗呢?
那年初中畢業,我考到成功中學。由於 我母親在「建國」中學教書,因此,根據學校規定,我可以到「建國」中學借讀,於是,我便從第三志願跳到了第一志願。高一的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倒數第二名。 上化學課時,楊義賢老師讓我上講臺去平衡化學方程式,我做不出來,楊義賢老師說:「你看你這個不肖之子,你母親是教化學的,你都不會。」
台灣地區的高中到高二分社會、自然兩組。自然組主要就是學習理工醫農,社會組就是學習文法商,通常都是比較差的學生學社會組。當時,我高一的英文和數學 都不及格,很擔心被留級。由於老師通常不會為難轉到社會組的學生,所以到了第一學年結束時,我就決定轉到社會組去。當時26個班,有2個班屬於社會組,那裏基本上是接收了高一被淘汰下來的所有殘兵敗將。到了高三分得更細--甲(理工)、乙(文)、丙(醫農)、丁(法商)四組,我念的是丁組。
高中跟初中完全不一樣,沒有初中以前的那種壓抑與不順。雖然到了這個比較好的學校,但還是進了類似「放牛班」的社會組。社會組的同學有相當比例的是黑社會幫派的混混,但基於初中時的經驗,我和這些同學相處得倒挺好。
我在高一、高二時不用功念書,主要是心有旁騖。由於初中時個子小,常常被同學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趕緊學打拳--螳螂拳,準備和同學打架用的。老師衛笑 堂是山東八步螳螂拳的嫡傳弟子,也是個老拳師,功夫極高。我雖念書不用功,但打拳卻極用功。當時我很厲害,班上包括混混,沒有幾個人敢惹我,除非他想挨揍。那時,我簡直得意極了。高一升高二暑假時,我和另一位同門師兄弟王國光到臺北的鬧區西門町逛街。當地幾個地頭蛇看我們不順眼,上來找麻煩,我們就和他 們打起來了,結果一下子衝出來一批他們的弟兄。當時真可以說是血戰一場。我的螳螂拳這時發揮了威力,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當時,周圍有上百人圍觀,我感到 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手腕也被打成重傷,養了兩個月才好。我們班上的混混也從不同管道得知了這個消息,最後大家乾脆開玩笑地叫我「西門町之虎」。
當時,我們社會組大部分同學的水準還是很差的,但我到了社會組還是最後幾名,怎麼念就是不開竅。到了高三,我才開始很用功地準備高考,但努力念了一年,還是一直沒什麼開竅的感覺。最後,很勉強地掛了車尾考上了台中市東海大學經濟系,那是一個相當差的學校。
二、從本科到碩士:「大牌學生「的體驗
我為何會一生鑽研學問,我想這和我大一時的境遇有關。我們經濟系有一門課程叫微積分,是跟化工系一起念,因此要求很嚴。該門課程總共8個學分,要念兩個 學期,而且一個學期得考4次月考。我第一次考了60分,但還是照樣玩。結果第二次月考時,我就想走快捷途徑,作弊抄鄰桌同學的試卷,結果運氣不好,被教該 課程的王文清老師抓到了,最後得了個0分。第一次60分,第二次0分,平均起來是30分。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會被淘汰,我那時就想放 棄了,因為就我的水準而言,哪有可能考100分啊。但這一次卻是我一生的重大轉捩點,我也不知道為甚麼,突然決定好好地念。每天很用功,念到半夜兩三點, 我當時就有那麼一根筋不對勁,我就不信考不過。結果念了一個月下來,突然對學習產生了濃厚興趣,我也突然發現微積分竟然也有很多樂趣,而且發現很多解不開 的題在解開時會很有成就感。第三次和第四次兩次月考考下來,我的平均成績竟高達99分。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沒那麼笨,這是我這一生第一次有這種美好的感 覺。結果一通百通,接下來的其他科目例如經濟學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從此以後,我就是全班的明星學生,而我自己當然也不客氣地以大牌學生自居。從那時起,我慢慢開始對做學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以後,我在學問方面博覽群書、涉獵極廣,尤其是歷史、政治、軍事和哲學四大科目是我有系統學習的主體。 我似乎從書海中尋回了自己的靈魂。只要每次回台中,我都要看望王文清老師,感謝他那次抓作弊抓得好,是他改變了我的一生。
由於 自己是大牌學生,因此和老師的關係也處得相當好,因為老師都比較喜歡好學生。到了大二時,石齊平老師和我聊天,他指出中國人念主流經濟學很困難,因為中國 人根本不是外國人的對手,只有念兩種經濟學學科,才可以有機會和外國人對抗,第一是中國經濟史,第二是數理經濟學。我的另外一位老師羅台雄教授更有趣,他根本就不認為我們中國人有任何可能在任何經濟學領域跟外國人對抗。他的名言是:全世界95%的文章是5%的人寫的,中國人只是點綴而已。在海外通用的本科 生教科書中,絕對看不到引用中國人寫的學術文章。
當時,聽了石老師的話以後,我也就不敢癡心妄想地學習主流經濟學了,我想鑽研 數理經濟學,因此我在大學時,輔修了很多數學課。但我總覺得自己的數學水準不是太高,主要也是東海大學沒有這方面的師資。另外,我對念中國經濟史還是有著 濃厚興趣的,但念中國經濟史就得先念日文,因為日本學者收集中國經濟史的資料比我們中國人還要完整。但在大學時期,學校根本沒有開設日文課程,因此這又形成了一個阻礙。我的數學未達理想水準,日文也沒有機會好好學,我實在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了,羅台雄老師的悲觀看法似乎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當時,經濟系的系主任是馬凱教授,他大概是台灣地區極少數的有信心的人了。我也不知道為甚麼,他從來就不懷疑我未來的學術成就。
在大學時,我對經濟學很著迷,曾經幾次寫信給一些很有名的經濟學大師表示我的崇拜之意,偶爾我也會接獲回信。當時我就想如果我當大師以後,學生給我寫信,我一定會回覆。現在,很多學生給我寫信,我都會盡量抽空給他們回信,以償我當初的夙願。2002年下半年,我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做演講時,很多學生圍著我,問的都是 比較淺的問題,我絲毫不介意,我還很鼓勵同學們多問問題。有些好心的教師怕我為難,連忙阻止同學發問,我說沒有關係,我覺得他們的問題比我年輕時問的問題 有水準多了。當我離開時,圍著我的學生非常依依不捨,我和每個人握了手並拍拍他們的肩膀表示鼓勵,學生非常高興,覺得深受鼓舞。那裏的同事問我為何對學生這麼好,我說我當學生的時候就曾因為大教授的那麼一點點關懷而大受感動,甚或終生都想以經濟學為追求的目標。我記的,當時普林斯頓大學和紐約大學的經濟學教授William Baumol給我回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話讓我終生難 忘,「A person with your eagerness can produce the new idea we need for the future「, 就是「像你這樣有激情的人,一定會研究出經濟學需要的新概念「。這句話我放在心裡一輩子,深受感動。William Baumol後來成了我在紐約大學的 同事。
大學畢業,我順利地考上了「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那應該是台灣地區最好的經濟學家的搖籃。台灣地區的政界人物幾乎都出身於「國立」台灣大學的法律系,而財經界人物則大部分出身於「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那一屆「建國」中學社會組可以說是獨霸經濟學家黃金榜,有好幾個同學目前都是臺灣地區著名的經濟學家。例如「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朱敬一;高雄市財稅局長、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中央」研究院院 士、「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計量經濟學泰斗管中閔等等。父親深深以我為榮,到處吹噓我的學歷,直到那個時候,他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身的。父親的反應也稍微太慢了一點,10年以後才搞清楚兒子在初中時幹甚麼。
我在「國立」台灣大學的指導老師--陳昭南教授,可以說是台灣地區經濟學泰斗。他在芝加哥大學師從國際金融大師蒙戴爾(Mundell,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由於他的英語口語不太好,因而沒有留在美國教學,在 20世紀70年代中期,回中國臺灣地區發展。我親眼見過他在臺灣地區篳路藍縷地開拓經濟學的研究。當時,他在「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一職。由於 他想在美國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因此要求該所買打印紙,該所竟斷然拒絕,表示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沒有人可以在海外發表論文,所以不用麻煩了。逼的陳老師不得 不自己買打印紙,爾後自己列印。投稿過後幾個星期,陳老師每天在送信時間一到時,就坐在樓梯上等郵差。但是大部分的回信都是拒絕信,在海外投稿實在太難 了。陳老師最為學生所佩服的一點是他從來不氣餒,他不斷地修改自己的文章,精益求精。經過大約20年的苦心經營,他終於替自己,也替台灣地區的經濟學界開 拓出了一片新天地。陳老師在經濟學主流期刊發表了多篇論文,而使自己成為了貨幣學中「兩種貨幣沒有完全替代性」的宣導人。而「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在他的影響下也慢慢形成了追求發表學術論文的風氣,最終成為「國立」台灣大學最引以為傲的學系。我認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的學術水準在亞洲地區也是可以拔得頭籌的。
研究生畢業之後,我就結婚了,而後按規定服義務兵役。我當兵退伍以後並不想去海外的,我只想待在台灣和太太兒子過小日 子。退伍以後,我在向陳昭南老師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申請工作的同時,也向我的另外一位老師于宗先教授主持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申請工 作。但兩位老師都認為我不是做學問的料,所以都拒絕了我。最後,是因為我和于宗先老師的一番對話讓我決定待在臺灣的。于老師認為我的學術水準有限,特別勸告我,學術研究是一條很辛苦的道路,他認為我最好考慮去公營銀行或外資銀行做事比較適合。他告訴我當學者就要像他以前的一個學生李志文一樣,執著、聰明、 努力、有悟性才行。像我這樣浮浮躁躁的就不行。李志文日後在沃頓商學院會計系做過三年訪問學者,我和他有過一些接觸,他也算和我有點師生關係。李教授後來 轉赴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任教。他也經常到大陸,主要在北京清華大學義務任教。
不知是可喜還是可 惜,我的銀行求職意向均以失敗告終,沒有一家銀行願意要我。如果真找到銀行的工作,我肯定就得在臺灣待下去了。因為找不到其他工作的緣故,於是我就去當記者了,整天跑新聞。在台灣和大陸類似,記者不被年輕人當成一項終生的職業,通常做個兩三年就會徹底轉行。我前前後後做了兩年的記者,也是考慮該轉行的時候 了。但因為我到處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所以只有考慮到海外留學了。
三、博士階段:沃頓商學院的煉獄式經歷
跑新聞實在太忙,我也沒時間念託福和GRE。最後,就只有隨便考了。託福我考了550分,在台灣地區算很差的了。GRE考了1640分,總分是2400 分,也是相當差的了。我當時向好幾所學校要申請表,芝加哥大學寄來了一頁黃色的表格要求我填寫從幼稚園開始一直到研究所的所有的成績,而後他們再考慮要不 要寄申請表給我。哥倫比亞大學也是要求我先證明我有實力申請該校,否則他們不想浪費申請表。最後,我只申請了7所美國大學。但我的運氣不好--只有一所學 校有回應--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而且沒有獎學金。年輕的我當時也慌了神:看來老師說的沒錯,我是沒有甚麼前途了。唯一一家願意接受我的學校,竟然 是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的、不知道有多爛的學校!真的,不是說笑,我到了沃頓才知道這所學校原來是大名鼎鼎。現在,大家對沃頓是婦孺皆知,沃頓的名聲如日中 天,令人仰止。不過20世紀80年代初的台灣消息閉塞,很少有人知道沃頓。
沃頓--爛學校--去還是不去?還有20000美金的學費,我依稀能感受到當年的猶豫和彷徨。可是,我的母親對她兒子的能力有著「莫名其妙的信心」。1983年台灣和現在大陸的經濟水準相仿,當時我們家有兩幢房子,其中一幢我母親把它賣了20000美金,準備給我留學交學費用的。可是,我的父親還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母親講:「你放心,我下個月就還你,我發誓還你。」還好,母親長了心眼兒沒有借給他。如果借給他的話,到現在我還再等著那筆錢留學呢。
我想當時為何沃頓會收我,應該主要是因為我當時申請了商業經濟系。當時,真正想讀經濟學的學生就直接申請經濟系,而想讀金融學的學生就直接申請金融系,商業經濟系似乎是一個很冷門的系,沒有多少人申請,所以機會自然比較多。而且當時沃頓的政策是國際化,所以也希望多收外國學生,這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至於我為何會轉讀金融系,那又是一個巧合了。當時商業經濟系的系主任要求每一個學生都要考微積分資格考試,我立刻就慌了手腳,因為我早就忘記了微積分。萬般無奈之下,我只有到各系打聽,看看哪一個系不考微積分。最後,終於找到了金融系。該系要求太嚴格,有一半的學生在第一個星期就自動退學了,所以有很多的空缺,於是就收了我。如果我當時直接申請金融系的話,那麼我被錄取的可能性不是接近於零而是等於零,因為每一個申請人除了我以外都是各國的天之驕子。
當時,在東海和台大總覺得自己的水準不錯,但到了真正的學術殿堂才發現這裏的課程太難了,根本聽不懂。而且,我們還是跟經濟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兩門課。那就別提有多難了。宏觀經濟學的老師是國際上極負盛名的日裔美籍教授Ando,他和Modigliani教授共同提出了現代消費理論 (Modigliani教授後來還因為該消費理論和金融學理論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該理論認為我們的消費不取決於我們今天的所得而是取決於我們未來 的永久所得。因此,你雖然今天收入少,可是你還是會向銀行借錢買房子或買車子,你的消費肯定超出了你的收入。這個借貸的行為就是該學說的有力證據。但這位老師教書的能力奇差無比,我們根本聽不懂他講的日本式的英文,而且他的指定讀物竟然超過了400篇論文,大家根本沒有可能在一個學期內讀完。該學期過了以後,我們大家問他為何教得這樣差時,他的回答令我們驚愕--他說博士教育就是為了培養那些能在困境中生存的學生,他是故意讓大家聽不懂的。他的這種邏輯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另外一門微觀經濟學,一開始就搞博弈論。我不知道讀者是否看過《美麗心靈》(The Beautiful Mind)這部電影?就是裏面那個有神經病的納什(Nash)揚棄了博弈論。他的理論幾乎完全打破了我們的傳統觀念。美國學術界以前總認為當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極大化時,那麼整個社會的利益就是每個人的利益的加總,因此也將會實現利益極大化。因此,政府不需要干預,只要讓人民自由發展即可創造出繁榮的經濟。奉行這個理論的當以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弗裡德曼(Friedman)和哈耶克(Hayek)為代表。我在上大學的時候,還和這兩位大教授通過信,他們兩位都給我回了信。弗裡德曼告訴我要成為成功的經濟學家就一定先要把數學學好。而哈耶克當時已退休住在奧地利薩爾斯堡,他是唯一一位以手寫信回復我的教授,而且回復了我兩次,我當時好感動。他也鼓勵我要多學數學。他說他的年紀太大了,無法幫助我了,他還推薦了一位在艾奧瓦大學的教授幫助我理解他的理論。很可惜,這些信我當時都沒有保留。
當時我是第一次接觸博弈論,之前,我簡直連一點概念都沒 有,而且我對宏觀經濟學也是消化不良,兩門課考下來,成績都是C。到最後,我這個人品行不錯,操行很好,上課從來不遲到、不早退。助教幫了我一個大忙,幫我改了個B-,讓我留了下來,因為在那裡,C是生存不下去的。那時,我不敢交學費,學費一直拖到最後才交。我想如果實在不行的話,乾脆拿錢回台灣算了,也 不用浪費學費了。所以學費一直從9月份拖到了12月份。
我總覺得沃頓的老師個個都喜歡打擊我們的信心。當時,金融系錄取我的系主任Santomero是一個著名的貨幣學家。我們上他的貨幣學課時他叫我們讀一篇芝加哥大學Metzler教授的成名論文。那篇論文指出如果物價上升,則資產價值就會下降,結果就是消費減少。Metzler教授就因為這一篇文章而在他27歲時拿到了芝加哥大學終身制教授的榮譽。Santomero 說:「27歲就是你們班現在的平均年齡。「接著Santomero很鄭重地告訴我們,「有一天Metzler發現自己長了腦瘤而必須開刀動手術,但是手術 做得不好,傷到了他的腦神經,結果手術後,他的天才就消失了,他的智商就變得像你們班的同學一樣了。」
我還記得我們上了一門很 難的課--股票期權。當上這門課的時候,我們發現全班年紀最輕的就是老師--AndyLo,他20歲出頭就拿到了博士學位。由於這門課的數學推導相當艱難,不是普通的微積分,而是不確定微積分(stocha sticcalculus)。因此,全班同學天天開夜車解數學題以應付該課的數學推導。Lo看我們的水準不行,特別講了一個故事以鼓勵我們。
斯坦福大學裡有一個博士生,成績相當差。他修課的平均成績未達標準並且已經準備走 人了,除非現在修的這門課可以拿A才能彌補一切。到了期末考試時,這位老兄連開了幾天夜車看書到半夜,希望可以拿個A。但由於讀書讀得太晚了,早上起來時 已經10點了,而考試早在9點就已經開始了。他騎著單車趕到教室已是10點30分。任課老師說:「我也不想為難你了,還是給你兩個小時的時間,你自己到圖書館裡去答題吧。考卷上有兩道題,黑板上也有兩道題,你把這些題目抄下來就趕快去圖書館。「兩個小時以後,這個可憐的學生將考卷交給老師,然後大醉一場。 因為他只答出了黑板上的一道題和考卷上的半道題。他心裏想,就算他答的全對也不過是40分而已,離A遠著呢。晚上,他匆匆地收拾行囊,準備第二天趕早上的火車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不到8點,他就接到系主任的電話,叫他立刻趕到系主任辦公室。他嚇壞了,不知道自己闖了什麼禍。趕到學 校,他忐忑不安地進了辦公室,那裡有系主任、任課老師和一位大師級的講座教授並坐著等著他。這位學生坐下後,系主任開口問他:「黑板上的這個題目是你自己 做的嗎?「他很害怕地點了點頭,他擔心會不會因為答得太差,學校要他賠償學費。三個教授輪番問他問題以確定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答。到最後,終於確認了。系 主任說:「斯坦福大學決定立刻授予你博士學位,並聘請你為終身制教授。「這位同學嚇壞了,在5分鐘後,他怯生生地問了一句話:「為什麼?「系主任告訴他, 黑板上的那道題他答出來了,而那正是愛因斯坦答不出來的題目。Lo問我們:「你們知道這位同學是誰嗎?「我們全班同學一起搖搖頭,Lo說,「他就是運籌學 之父--George Dantzig。」
我們用兩年的時間把所有的課程都讀完了,同時還得通過四次非常困難的學科資格考試。考完試以後,即被授予金融學碩士學位。這四次考試中最難的就是第一次,因為要考宏觀經濟學跟微觀經濟學。我當時是全班第一名考過的。一直到了這個時候,我才覺得自己讀書開竅了。
而第四次資格考試是考金融學的專業課程,其中一科就是Lo的股票期權。為了準備這次考試,我們全班昏天黑地地開夜車解答艱難的期權數學問題。但我們拿到考卷時,一看只有一道考題「股票期權可否兌現」,題目雖看似簡單,但老師卻給了我們8個小時的答題時間。我們都認為8個小時解這一道題,那它肯定是很難的 題目。我還記得全班8個小時內無人提早離場,個個洋洋灑灑地寫了至少40頁以上,我大概寫了60頁。考完以後,老師告訴我們,全班都答錯了,答案是-- NO--老師只要我們回答一個字而已。全班唉聲歎氣,果然是小鬼難纏。
我到了沃頓後,碰到了初中時代的同學--馬學勇。他在 「國立」台灣大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以後,拿著全額獎學金赴沃頓商學院決策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當然,他不記得初中那一點瑣事了。他還邀請我參加了他的婚禮。但一兩個學期以後,他就不讀了,聽說是考試沒過關。但他也沒有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就這樣消失了。據同系的學弟梁定澎(現任台灣「中山大學」教 授和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教授)的說法,馬學勇這一生太順了,所以沒有辦法承受打擊,因此輕易地就打了退堂鼓。事實上,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壓力太大了,而且總把讀書看得太重要、太唯一了,幾乎沒有辦法擺脫這個枷鎖。老美就輕鬆得多,念好就念,念不好就不念,無所謂。我們可能認為馬學勇無法承受打擊而退學,說不定 他自己可能就像老美一樣覺得念書沒什麼了不起的。所以也可能並不是他本人想不開,而是我們局外人在替他想不開而已。
1985 年,在沃頓開始寫博士論文時,我只想做投資學方面的論文,我根本就不敢做公司財務的課題,因為我認為自己是不適合這種軟科學的,我也不認為我能進那個小圈子。只是當時沃頓的一位元大牌教授Irwin Friend需要一個勤勞的打雜工。由於我曾義務幫他搜集了一些資料,所以他很希望繼續用我這個廉價勞力,因 此就收了我,並要求我做公司財務的實證研究。從此以後,我就開始了噩夢生涯。
當時,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找公司財務的論文題目, 更不知如何著手,只是很努力但很幼稚地想把論文寫好。我想可能是我的「勤勞」感動了他,他指定了一個公司財務的題目給我,同時也把有關的資料給了我。在他 細心的指導下,我很勉強地把論文在半年之內寫出來了。我總共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拿到了金融學博士學位。這個速度就沃頓創校一百餘年的歷史而言,可以說是非常 快的了。
Source: 獲作者授權,轉載自極視傳播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你點睇?】媒體近日報道有關愛隊涉活動造假或誇大以滿足KPI,事件會否影響你對關愛隊的印象?► 立即投票